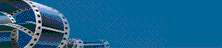初春的蓉城之夜尚存寒意,可2013年1月15日晚的成都锦城艺术宫却气氛十分热烈:“非常梦想”——四川省首届农民工原创文艺作品大赛颁奖晚会在成都锦城艺术宫举行。
244件获奖作品的作者荣登领奖台,接过颁发的奖杯和献上的鲜花。来自盐都自贡的打工诗人印子君的组诗《我用每一句诗行抵达成都的心脏》荣获文学类一等奖。这也是印子君继2008年获得《星星》诗刊举办的首届全国民工诗歌大赛大奖之后,再次荣膺同类文学奖项。本次大赛于2012年10月启动,由省人社厅、省文化厅、省农劳办联合主办。大赛组委会共收到5000多名参赛者的13000多件作品,经综合网络票选和专家评选,按类别分别评出大赛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打工诗人印子君系自贡市富顺县琵琶镇人,1987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1988年底进城务工,属改革开放后早进城的农民工之一。
印子君出身于极为穷困的农村家庭,5岁丧母,年迈的祖母和父亲伴他度过凄风苦雨的童年。他自小就随大人参与田地劳作,耕种犁耙挑抬样样在行,养成了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不畏困厄的品性。
上中学后,父亲十天半月要爬30多公里山路为他筹钱送粮,每次送父亲回家,望着父亲渐渐消失在残阳中的背影,他都想哭。
然而上高二的印子君却发疯似爱上了诗歌,见诗就读,见好诗就抄,读得多了,就试着写起来,以至“不务正业”,断送了大学梦。
正是多梦时节,印子君1987年从富顺县第三中学高中毕业回到了琵琶镇黄家村,乡里的负责人见他颇有些文才,便安排他在黄家村小学任代课教师,因代课待遇实在太低,万般无奈,一载寒暑过去,他仍回家干起了春种秋收的农务。
1988年岁末,印子君以“合同工”形式进入县城自贡市变压器一厂一家私企任厂办室文秘工作,一晃,6年青春岁月飘然而逝。
怀揣着对未来的期盼和对文学的梦寻,印子君怀揣着梦想踏上背井离乡的火车,1994年10月初,27岁的印子君到北京亚运村安慧里大红灯笼涮锅村一餐馆打工,负责采购工作。每天,他骑着一辆脚踏三轮车去农贸市场,寒冬腊月,北京气温一般都在零下世几度,大清早逆风而行,脸像被锋利的刀子割着一般,两只握着车把的手尽管戴着手套,还是冷得发痒发麻。
和所有农民工一样,残酷现实时时将美好生活的梦想砸得粉碎。绝望时,唯有对文学的痴迷,让他扬起了生命的风帆。
每天晚上,他工作的饭店关门后,他便来到自己租住的小屋,读诗,写诗。在写诗的同时,更加关注现实关注人,他把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对人生的感悟凝聚在诗里,使他的诗里多了一份凝重与思考。卷缩在出租屋里,他写下了了这样的诗句——《亚运村》
“许多球汇聚于此/成为一种景观/一种话题/他们/有的是被抛来的/有的是被拍来的/有的是自己将自己投来的/更多的/是被踢来的/我/属于足球……
一道叫安慧里的门/防守很严/我轻易被挡在了门外/至今/仍在一些脚上/传来传去”。
这首题为《亚运村》的诗,将球的波动与人的流动交织成一体,把打工族的生态、心态展示得淋漓尽致:这里的“球门”,是机遇、希望与成就的象征,他被“挡在门外”。在他的诗里,虽不见汗珠、泪珠,一份生存的体悟与生命的感悟早在被“传”的过程中渗透。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披阅古今中外名人的人生,抚案叹之,感慨万千,难怪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不经受磨难的人非真英雄,由此看来,幼年时贫困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笔精神财富。
冬去春来,打工之余的印子君笔耕不辍,创作了一系列优秀作品,其不少诗作次第见诸北京及全国各地报刊,部分作品还被选入国家级权威选本,他的诗作逐渐受到评论界注意和肯定。
与此同时,印子君的创作和生活也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光明日报》《生活时报》、北京电视台、《诗刊》、《四川政协报》《四川青年报》和《自贡日报》等,先后以专栏、专题和专版的形式给予连续报道,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也更加坚定了本人的文学志向和创作决心。
京漂四载,带着辛勤劳作的酸辛和工余笔耕的硕果回到了家乡,
1999年7月,他先后到成都在报社、文化出版公司和杂志社上班,2003年始,他受聘在成都《龙泉驿报》做编辑工作。
数载打工岁月,风雨兼程,飘然而逝,唯有对诗歌的辛勤耕耘,让他收获了《夜色复调》(组诗)、《身体章节》(组诗)、《青城曲》(组诗)和《古典音乐》(组诗)等诗作。并著有诗集《灵魂空间》《芙蓉锦江九人诗选》(合著)。还有幸成为了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微型小说学会副秘书长。
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必须根植于生活和大众的沃土。只有这样,作品和作家才有丰厚的营养,强健的筋骨和充盈的血液,从而使其作品更加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回首古今风流人物,哪一个不历经千辛万苦而将自己的价值展现给世人看,又有几人能看到辉煌背后隐藏的辛酸与泪水。范仲淹两岁丧父,随母远嫁,幼时读书甚至连一碗粥都难以吃到;司马光亦出生寒门;荷兰画家梵高也曾两袖清风,生活上常常需要邻居热心的救济。而从这些伟人所创造辉煌的背后,却是忍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身体作战。也正是因为他们承受住上天所赐予他苦难的一切,最终才让苦难变成一笔精神财富。
2002年初春,家乡作协在富顺举行了“印子君诗歌作品研讨会”。
《星星》诗刊常务副主编,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诗人张新泉在会上热情洋溢底讲到:印子君作为一名诗歌写作者和打工者,经受着社会变革带来的对世界的重新认识和陌生化的人生难题,却始终微笑热情地面对生存和生活。难能可贵的是,印子君将富顺文化中的执着精神与亲和关怀贯注在写作与对人处事中,锲而不舍地追踪着、研究着当代文学演进中的诸多问题,以此丰富自己的思考和写作。他的诗因其以一颗平常心发掘出琐屑生活遮蔽下的温馨,平凡覆盖下的生命价值,为亲情和乡情注入了易被人们忽视的人生况味和文化意义。
印子君为人厚道,诚实正直,与当今文坛上的一些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的作品研讨会在故乡召开,意外地收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的贺电和《诗刊》编委、著名诗评家朱先树寄来的评文,这对于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是至可宝贵的。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现为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在寄来的评文中写到:欣闻印子君诗歌创作研讨会在蜀召开,谨致热烈祝贺。认识印子君,是从读他的诗开始的。那质朴无华的诗句,每每读来便感到如闻乡音般的亲切。子君是川南的灵山秀水孕育的乡土诗人。他的作品语言平易简洁,感情真挚热烈,饱含着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情,对家乡的无限眷恋。正是具有至真至切的情感,才会有这亲切生动、韵味悠长的诗句,才会有这发自心灵的歌唱。
中国作协《诗刊》编委,著名诗评家朱先树在寄来的评文中写到:在商品社会,靠过于纯粹的诗歌来改变生存命运和生活处境,的确是很困难的。但诗可以成为一种精神的支撑,让我们的灵魂空间充满诗情,人生就会有更多美好的向往,生活自然也就有了品位。我以为印子君对诗歌的爱好与创作追求是可以证明这一点的。
一个好的诗人应该是一个语言的魔术师,从他的口袋里展现出来的永远是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九十年代以来,诗界对诗歌语言的探索风靡大地,但成就并不明显。一方面,肆意的解构不仅解构了诗歌的精神,更解构了诗歌的语言,语言传统的能指和所指的关联被打破,大量私人化语词和长距离断裂的搭配充斥诗行,使诗歌成了艰涩难懂的梦呓。另一方面,对个性张扬的极端追求使诗语言成为向读者变相邀宠的工具:“下半身”依靠暧昧的性词汇吸引了一阵眼球之后很快沉寂,“80后”打着率性而为的标签把诗语言变成了个人的狂呼乱叫,而所谓的“梨花体”更是把“口语”变成了“口水”,畸形发展到了极致,把诗歌变成了语言的垃圾场。
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地域写作的背景,印子君的地域写作背景,就是深深植根于自己脚下的那块土地。诗人李自国曾这样评价印子君和他的诗作:土地赋予了诗人开阔的胸襟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印子君的诗就是在辽阔宏大的时空隧道中穿行的大地之花。它使我们拉近了与《世界》相处的距离,聆听到《教堂》里传来的那悠扬的钟声,从而让我们抚触到《白夜》里的脉温与跳动。
印子君是一位默默而潜心创作的诗人,这些年,从他在《星星》等刊物发表的作品来看,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在漫漫诗途上迈着的坚实步伐,无论在题材、风格还是手法、技巧上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可贵的拓展,常能令人耳目一新,展示了一位走向成熟的诗人的进取精神、求新意识和创作实力。于此,我们有理由期待他走得更远。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现执教于西南石油大学的青年诗评家李民盛赞印子君的组诗《古典音乐》:好的诗歌一定就是一首好的乐曲,好的音乐和舞蹈本身就是一首诗。印子君的《古典音乐组诗》,是一条很好的诗歌创作路子,她延伸了诗歌的能量空间,推进了艺术门类的渗透,拉近天国和我们的距离。
印子君的诗作和那些故作声势的诗歌不同,作品文本的冲击力完全是基于诗歌语言的角度扑面而来的:空灵而不浮靡,清新而不稚嫩,独特而不张扬。表面看来,他的一组组诗作的语言是接近口语化的,没有艰涩的意象,没有远距离的词语搭配,但是这种近似口语的语言却显示了诗人高超的文字组织能力和写作技巧。
2008年初春,著名作家李锐、蒋韵夫妇到自贡寻根,并在富顺凤凰山庄与富顺文学爱好者见面,蒋韵随手翻阅着一本《富顺文学》发出感慨:“富顺这个地方真不敢让人小看,在一个小刊物上,可以看到了不起的好诗!”说着,她轻声读出印子君的诗句:“如果夜色突然喊出我的小名,那我不再仅仅觉得/夜色离我很近,显然,夜色还跟我很亲……”继而她赞叹:“真是很美呀!”
印子君的诗作中有不少抒写乡思的诗歌,由于长年“飘”在异地,对乡土、乡村的眷恋使他禁不住一次次回望,而讨生计则需要他在了无尽头的路途上前奔,于是,他的诗行便成了身的分离与心的回归的一个平衡点,所有的情感和无奈都凝结其中了。
印子君是热爱文学的“草根辈”,他渴望有一片绿茵茵的大草原那么宽广的时空来放牧缪斯,但是,生存状况则不断提示他要热爱劳作,要不吝惜付出淌汗劳力,唯有一份耕耘,方得一份收获。
长期以来,印子君的工作总是属于戴有“临时工”的鸭舌帽的“编外”性质。在《大地》(组诗)中的《龙泉驿》一诗里,他噙泪调侃:“出了东门,经净居寺,过沙河堡/大面铺伸手,握住一介落魄书生/他满脸秋色,却不为赴京应试/仅作借道还乡,但了无衣锦……”他郁郁不得志的落寞,如飘散风间的一乘一乘蒲公英种子的小伞。
虽属草根,身处底层, 令人欣慰的是,印子君始终坦然面对严峻的生存现实,潜心创作,近年来的诗风嬗变和相继推出的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昭示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卓立不群的诗风。
夏日的夜,梦一般的美。星月之下的世界魅力万千。
黑夜遮蔽了一切,但同时也包含着一切,它无疑蕴含着生命的原色。子夜时分,诗人印子君蜗居成都龙泉驿的寓所,此时此刻,他悄然躲进沉寂的夜色,温顺地拥抱着夜色的安抚,遥望窗外浩渺的星空,诗情汹涌,笔走龙蛇他的笔舌便汩汩流出心灵深处的奇光异彩。——
夜色有一颗钻石般的灵魂
夜色有一颗钻石般的灵魂,它覆盖着我金子般的记忆
在夜里,只有夜色悄悄为我传递着,今生与前世的消息
夜色总把自己像大海一样铺开
铺出无边的宽厚,铺出深深的静谧
坚定的夜行人,被夜色视为朋友和兄弟,一一珍藏在心里
哦,星月在浮动,花草在微语,虫鸟在低吟——这是夜色的呼吸
而经由晨露洗浴,夜色将变成一群群夜莺
从屋顶和树梢缓缓飞离
夜色有一颗钻石般的灵魂,它覆盖着我金子般的记忆
在夜里,只有夜色悄悄为我传递着,今生与前世的消息。
诗作落成,打工诗人印子君又陡生激情,突发灵感,给诗歌写起了一封“倾吐自己的心曲”的信——
亲爱的诗歌:你好!
请原谅我以书信的形式与你交谈。原本,我们每天都在相见。
与你相识,是1986年的夏天。那时,那么多人都在追随你,都在投奔你,都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靠近你、讨好你。凡你所到之处,都会引起震动;凡是有你的地方,无不热血沸腾、豪情万丈。可以这么说,只要有你的地方,就是山呼海啸、人潮涌动、激情四射的所在。那时,你成了那么多人拥戴、顶礼膜拜的神,你自然也成了我的神。虽然,我对你的爱,没有任何充足的理由,但我就是在当时那种背景下,阴差阳错地爱上了你。现在细想起来,我也真够大胆,全然没有顾及自己的潦倒、卑微和浅陋。是的,你就是这样,始终就是这样,对所有爱你的人,你从不拒斥,敞怀接纳,一如对所有离开你的人从不挽留。
诗歌,是你教会了我宽容、大度,是你教会了我隐忍、沉静,是你教会了我多情、善感,是你教会了我敬畏、虔诚;诗歌,是你让我懂得了天、地、人,是你让我懂得了真、善、美,是你让我懂得了恭、谦、让;诗歌,是你让我认识了神、鬼、兽,是你让我认识了假、丑、恶,是你让我认识了羞、耻、辱;诗歌,是你使我看见了昨天、今天、明天,是你使我看见了秘密、奇迹、怪诞,是你使我看见了永恒、无限、渺远,是你使我看见了短暂、迅疾、瞬间……
诗歌,我与你的相逢也许是一种偶然,但我对你的爱却是必然。在这茫茫尘世,因为与你结识,我始终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是你,给了我觉悟,给了我信心,给了我力量,使我有勇气面对自己,使我有信念战胜自己。我对你的爱,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缓慢的、悄然的,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推进的,甚至有些谨小慎微和诚惶诚恐。谢天谢地,毕竟,我最终全心全意爱上了你!你在一些人心里,可能是情人、恋人或妻子,而你在我心里,有时是母亲,有时是姐姐,有时是妹妹。你是最高贵的,也是最平易的。虽然你无处不在,但绝非每时每刻都能遇见你,你只可能跟爱你的人相见,你只跟与你有缘的人相识相知。
诗歌,通过你,我邂逅了那么多才华横溢、学富五车的人,他们是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他们就是留存在这个世界的稀有金属。他们有的在唐朝,有的在宋朝,有的在北方,有的在南方。他们有的在18世纪的欧洲,有的在19世纪的美洲,有的在20世纪的非洲。诗歌,是你消除了我与他们的种种隔膜,是你打通了时间的隧道,让我抵达他们的内心,触到他们的灵魂。是你,让他们充满活力,并且永远年轻。
诗歌,在你的门庭,已没有昔日的热闹和喧嚣,但你泰然自若,因为你依然是你,始终是你!任何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爱你还是不再爱你,他们都没有错。错的是,他们居然怀疑自己爱过你,后悔自己爱过你!事实上,你成全了他们、玉成了他们,也宽容了他们,他们却挟持了你、强暴了你、糟践了你!而我所能做的,仅仅是,一如既往地爱你,让我的爱更加本真,不受玷污,不掺水分!
在这个日益市场化、商品化、程序化、格式化、工业化的世界,诗或诗性其实就是人类最后的精神依托。因而,诗歌,你就是我们在这日渐沦落的尘世中最后能逮住的一根救命稻草!
感谢你,我亲爱的诗歌,是你让我感受到世界的美好和灿烂!
这是2010年6月8日深夜于成都龙泉驿的寓所信马由缰挥笔写下的文字。
这也是打工诗人印子君终为诗人最准确最贴切的诠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