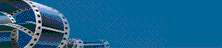诗人,从来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身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物种。作者创造作品,作品又反过来塑造作者本人。与小说家、散文家不同,诗人完成的作品,更富有生命体征:它由文字,以及文字世界以外的诗人的生命体验共同构成。风格是文字,更是人本身。一个诗人,还要活成一个诗人,这才算数。当我想动笔写写诗人李加建的诗歌,我却写下许多他的小说散文,他走过的路,说过的话。因这所有加起来,才是李加建的诗,是他最终完成的有落款的诗。
一"我熟悉这样的刺杀。有人专门训练过我。"
这一切对于新一代年轻人是隔膜的:无休止的革命,集体无意识的洪流,一轮轮战争的狂欢,热得烫手超出一己得失的理想,人性可能到达的纯粹或黑暗......这些都是大时代的专属,与这个不痛不痒的小时代无缘。大时代出大作家,小时代出小作家。像阿伦特指出的那样,二十世纪是战争和革命的世纪。中国革命经历了时间序列上的三部曲——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其中,最后一部历史车轮在诗人李加建身上完整地碾过。
诚如"法国大革命为其之后的每代人都留下了标记",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史也为"同时代人"盖上了 无法磨灭的胎记。李加建是不折不扣的"革命之子",他1936年出生于四川富顺县,12岁便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从事进步学生运动,13岁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小年纪便提枪挎剑,懂机械懂飞机,甚至懂摩斯码。革命和青春相互激荡,他和新政权同步成长。按说他应是革命的嫡系传人,然而未成年的他已然极端反感党内的告密之风。这些似乎都是一个巨大的铺垫,为他日后思想观念和人生道路的转折种下前因。最有价值的对革命的反思,往往来自于革命内部,近年出版的韦君宜《思痛录》、《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集》和萧军《延安日记》等等,都是"浓缩着中国共产革命中的巨大情感力量,尤其是那些具有个人英雄主义情结,更不用说自由主义情怀的文化人,在这场革命中的心情和命运"。在李加建日后所有的诗文中,深度理解革命,始终是他刻骨铭心的母题。无论是诗歌,小说或随笔,读来都有一种戳心的真诚,是的,戳心!其大量的文字都具有"口述史"的史料价值,诗歌也可以是口述史,说起来希罗多德算是口述史的鼻祖吧。我读文字,喜欢陈上一段岁月再去读,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文学思潮的统治和文学技巧的迷惑。这些"口述史",不同于当下暧昧的历史写作,它们有着明朗的历史观,同时有犀利的思想包裹,它们释放出极为复杂的历史信息和负能量,展现出革命宏澜下的暴力,冒险,炼狱与爱的悲剧。梁启超也曾一度赞同革命,但他很快意识到,社会革命碰不得。1958年,李加建被扣上了"极右派"的帽子,此后他长期暴露在体制与人性的残酷之下;而在此之前,他已是蜀地的名噪一时的青年才俊,且与当年的自贡第一美人轰轰烈烈的爱着。他们约定30岁之前不结婚,有太多的知识需要学习,他们立志为了理想自我隐忍,那是灌输到血液里的革命精神训练出的一代人的英雄主义。巴尔扎克曾抱怨法国人永远在写英雄史诗,可英雄从来不会深入到农民的生活。李加建用 人生和文字作出了中国式的反驳。在他的诸多短篇小说中,都有落难的英雄形象,比如《留得残荷听雨声》中形同古人的汪老夫子,《月落乌啼》中被认为是疯子的二少爷,《斜晖脉脉水悠悠》中飞身夺旗的外乡人等等。他们与农民并不隔膜,甚至与底层社会结构亦不隔膜。有研究表明,从明清到民国,中国底层社会基本没有变化,真正的变化是在1949年之后发生的。这些有着古典主义情怀和道德伦理界限的落难英雄们,感到隔膜的,恰恰是这些"真正的变化"。
在拉丁文的解释里,"革命"除了代表动荡更替,还先天性蕴含了复辟、轮回之意。李加建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常常处于不可抗性的命运轮回之中,这轮回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六道轮回,而是一种更具现代性的革命的轮回。比如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春归何处》中,林老师和火葬场的业余作者,交叉叙述数了两个处于不同时空的爱情故事。故事不断交织,人物命运的兜转和不详令两个故事获得了某种神秘意义上的感应联结。看似与过去做下了断,实则呼吸着一样频率的情感节奏,最终暴露出一个可怕的事实:社会革命摧毁了一切人,一切情感,一切原则。革命的惯性,会将这摧毁一路循环下去。小说的末尾,老画家的妻子拿出了亡夫留给她的画作,尘寰纷争之外的峰峦间,有一处古寺门,老画家曾对爱妻说过,"我如先去,必日日在此倚门等你",然而展卷之时,竟发现画中古寺之门已紧紧关闭,"记得当年,那门,是开着的呀......我将原稿往下翻,却发现下面又是开头那一页的内容",悲剧由此进入无止境的循环,火葬场业余作者笔下的"梦和诗养活不了的爱情"只是这悲剧轮回中的又一轮。在这些看似轻盈舒展的故事里,李加建用最轻的冷泪,拨起了历史的惰性。
二、"从解放全人类到解放一个人。"
2013年7月,我在四川《星星诗刊》的夏令营上,第一次见到了精神矍铄的李加建老师。他留着叛逆少年的齐肩长发,左手臂上有一个醒目的心形纹身,近80岁的年纪,腰板却像《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一样挺直到令其它人难堪,走起路来风生水起,大步流星,我们一群80后90后的姑娘小伙,都赶不上他的步伐。印象深刻的是,他挥动大旗,真心真肺地大喊:"诗歌不死,青春万岁!孩儿们,我爱你们!" 在场的梁平老师笑言,这话只有李老师敢喊,也只有他喊出来才是真的。大半年后,我在北京他的学生家里再次见到李老师,听他讲起过去的峥嵘岁月,才知他手臂上的那块心形纹身,原是一处刀疤。他被打成右派以后,长期关押,强制劳动,其间一位出身富商的青年护士对他深深爱慕,为了报答这份恩情,李加建将女护士的名字,用小刀刻到自己手臂上。两人日渐情深意笃,女护士死心塌地。李加建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自己一个大右派,什么也给不了,只会无尽地拖累人家姑娘,于是狠下心来,斩断情丝,当着女护士的面,拿剪刀剪了手臂上的爱印,一块肉甩了出去,以示决绝。
当我惊心动魄地听着这些故事时,李老师的太太也端坐在一旁庄重地聆听,她不时地纠正补充一些具体细节,仿佛在整理一段谙熟于心的历史。我看到他俩眼神的交汇中尚有柔情,这在老年伴侣中并不多见,几乎是一瞬间,我理解了李加建文字中漫溢的至柔则为刚,至刚则为柔的精神气质。
读短篇小说集《春归何处》,觉得是一场柔软的苦刑,不该被忘却的历史,经由一种返回古典的古中国文人情怀记录下来,血腥的同时缠绵悱恻,叫人着迷流连忘返。写爱情时,李加建的下笔是曹雪芹式的,墨中女子多着这可爱的灵魂,只是她们没有成为闲游在大观园中的尤物,而是不幸掉进了血雨腥风的泥沼。李加建对女性近乎宗教式的感情,可能来自于母亲的影响。他母亲出自农民家庭,在他父亲患病期间,曾经亲手割下自已手臂上的一块肉作为药引子为丈夫熬药。然而丈夫病好以后,却另结新欢迎娶小妾。这并没有引发一场家庭战争,反而引发女主人对这卖身为妾的小女子深切的同情,待她如同亲妹。李加建被划为“极右”,押送他乡服苦役多年,他母亲在贫病交加中长期等待儿子归来无望之后,忧愤压抑选择了自杀。大概是因为这一层,李加建成为了一个真正懂得女性的诗人。他诗文中有一大批叫人难忘的女性,比如《斜晖脉脉水悠悠》中的荷花,叫人不禁想起了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看着荷花划船,总使人感到愉快。她身材不算太高,却苗条结实,穿一件白底红花的小衫,一条宽大的蓝布裤子。" 这样一个质朴纯净的女孩,针线簸盖里藏着心上人送来的一枚弹壳,那是缅甸一役中,男人击毙日军的带血子弹。当荷花失去了她的爱情后,作者写道,"我尽量不去望那长满芦苇的河汊和灰包上的小屋,尽管和这个地方有关的两个人每天近在我的身边,我却感到他们只剩下了褪色的躯壳,那些曾经充实于其中的珍贵的东西,已经永远不存在了。"小说最后平地生出一笔,"我"无意看到几幅气韵灵秀的水墨白荷花,得知是一名七旬老翁所画,"我又问了那老同志的口音、身材、长相,心里越发沉重和不安",待探访时,得知老人一个月前已经去世,且终身未娶。小说中的爱荡气回肠,像在另一个世界——武侠的世界。李加建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古道斜阳》,就长期被误读为武侠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名字来源于易经八卦,其中刺杀乾隆的情节,直指专制政权中心,说它是一部武侠小说,不如说是一部革命小说。
武侠世界最迷人之处,在于它有一套与现行世界截然不同的生命观念,多数英雄好汉美女佳人,都是立时可死的状态,对于存在没有那么的放不下。除了生命观念以外,武侠人物的情感状态,也是另一种审美,与现世难容,却与上古的心灵质地相近。二十世纪以来,由于极权在许多国家的发生,单一的描摹现实已无法表现出"混乱的地狱",作家们不再如龚古尔兄弟,福楼拜,小仲马等人那样,追求对现实生活的精准刻画。各种现实的变形,在全球各大洲,依据其不同的民族性格生长起来。当李加建同代和后代的许多作家纷纷效仿拉美,或者走进"天鹅绒监狱"时,李加建在文学中收藏一个民族的品性。他的文学从而呈现出复杂的历史性格,它们既古典又先锋,情感状态趋于武侠,对现实的直击又是真刀真枪。他有多少现实关怀,就有多少玄思冥想;他有多少伤春悲秋,就有多少现实悲愤;他有多柔,就有多刚;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恨。阴阳六爻的消长,乃是中国的变形记。
在去餐馆的路上,李老师接过妻子手中沉重的行李,但凡上下楼梯都主动搀扶着她的胳膊,进门也请太太优先。他倒不是老绅士的派头,而是出于(讲出来似乎肉麻)内心的爱意。他同辈的知识分子平反之后,大多换了新式太太,弃了农村的发妻,"他们离婚说没有共同语言,我说怎么你从前落难时讲的是中国话,现在讲的是西班牙语,荷兰语?"李加建挽着妻子的胳膊道,"从前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后来我想我就解放一个人。"妻子生在农村,年轻时不识字,如今也开始写回忆录了。李加建摘帽以后,妻子才知道丈夫原来是个受人尊重的大知识分子,走在街上都自卑地隔开一段距离,默默跟在丈夫身后。李加建一手搂过妻子,不顾推搡,"信不信我敢在十字路口亲你?这又不违反交通规则。"他在他写的歌剧《月落乌啼》中反复咏唱:“作好身边事,珍惜眼前人。”他说:“爱是一种自我完成,一种宗教行为。悟到这点之后,我就活得踏实了!”
三,战争是人类兽性的大狂欢,
李加建很早就将笔触伸向了人性深处的美丽与恐惧。1985年,耶鲁大学教授用马来西亚农民的口述史写成了《弱者的武器》,他发现革命当中最大的暴行,还不是来自于极权者的镇压,真正精彩的是那些生活在强权统治下的弱者们的拖延、撒谎、使坏、倾轧......在李加建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对类似主题的深入探索。他的作品面向新的受众,寻找鲁迅之后重新思考"国民性"的角度和方法,在新的语言历史环境中发生新的意义。《月落乌啼》中,"疯子"二少爷和"清醒"的民众,几乎直接印证了福柯的名言"不疯癫,只是另一种疯癫。" 小说中,对疯子二少爷实行暴力和软暴力的民众们,是作者对"看客"文化的进一步的分类和深究。作者似乎努力回答着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常和许寿裳讨论的三个相关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对于第一个问题,李加建的回答是返回古典,一种整全的纯粹的人性,这也是他诗文中最为柔软动人的内核。作家中只有少数高手能在"人性"的描绘上,制造出陌生化的体验。而偶尔的陌生化又往往是建立在负面的冒险上,写坏人容易写好人难,像李加建这样呈现炼丹炉中淬炼过的人性,少之又少。对于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李加建似乎并不急于回答,他选择经由记忆之路,回溯到那些最为远离人性的时刻——战争,以此达到某种思考的纵深。
人性之中本就存在着神性与兽性,李加建一直说他要写一部有关战争的长诗。也许这是他最能驾轻就熟的题材。他十几岁时就扛着长枪出生入死,重返文坛以后,作为市文联专业作家,1985年欣然接受解放军总政治部邀请,远赴对越自卫战前线。当时军方的领导怕闹出娄子担待不起,将他安排在较为安全的前线指挥部采访,他断然拒绝,穿上军装挎起枪去了老山、者阴山、扣林山前沿阵地,和战士们提起枪来就和战士们一起经历枪林弹雨。我曾当面问他,打仗时害不害怕?他皱紧眉头,"在战场上什么民族、国家、军令,全都没那回事儿。当战友的鲜血溅上自己军装的那一刻,勇气就来了,就什么都不怕了,全杀红了眼。战争,就是人类兽性的大狂欢。”有人开玩笑说他是“爱国好战分子”,“不!”他说,“战争的正义与否历史自有公论;我关心的是战争进程中人的存在状态。”
兽性狂欢之后,神性一时难以归位。革命和现代性催生出了现代心灵的质地。哲学家马南,很早就注意到了现代社会中权利和意见的分离,国家和宗教的分离,事实和价值的分离,政治权力和自然权力的分离等等。事实上,这些分离政治同时肆虐了现代心灵,历史的惰性使得革命并未催生出更为灿烂的人性,相反,现代心灵面临着巨大的撕裂和困境,也暴露出更多的丑恶和不堪。李加建写过一篇叫人忍俊不禁的《名猪协会》,构思新奇,招招见奇,其中深藏的讽刺叫人细细咀嚼。他的短篇小说《捕星星的人》、《体验另类》、《有钱真好》等,也都是运用先锋的手法,直指制度挤压下的丑陋的现代心灵。他曾写道:"现在你到街上看看,猪、牛、羊满街走,狼隐身着,人却很稀疏。"
诗人的晚年,如他所言注定是沉重而苦涩,对这个民族的失望叫他常常半夜被冷泪惊醒,几次都有去撞火车头的冲动,家里的阳台也不得不安装了不锈钢护栏,他来信中感慨不知还能活多少时间?我则一心希望他能活很久,单是活还不够,要活得足够久足够久,直到目睹大街上的猪、牛 、羊又慢慢现出人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