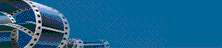一直以来,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都比较受当代作家关注,如何在创作中摆脱宏大叙事的模式,拓展抗战题材创作的空间形式,也一直是作家在创作中探索的问题。近日赵应的长篇小说《盐马帮》的出版(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6月),为抗战题材创作探索出新的形式,即将地域文化特色与民间传奇因素融于作品之中,以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视角对滇西抗战史做出了一段新的诠释,既展现了盐都自贡的地域文化的独特景观,又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盐马帮》以抗战时期滇缅边境腾冲县城的滇西战役为时代背景,讲述了马锅头云龙率领一队马帮通过史称“五尺道”的盐马古道,历经千辛万苦,通过重重关卡,向抗战前线运送自流井井盐的故事。作者从云龙加入袍哥会的传奇经历开始讲述,展示了自流井地区从事井盐生产和运输的文化特色,同时将那个时代不同阶层的人物对待抗战的心态做了深入挖掘,在爱恨情仇中揭示了人性的真善美。盐马帮的弟兄一路南行,从出发时的参加抗战到在腾冲前线目睹了日军的暴行,更加激起了马帮游击队参加抗战的决心,在与日军的几次战斗以后,马帮游击队全部牺牲。从题材角度讲,《盐马帮》是一部抗战题材的叙事之作,从故事的主体看又是一段民间化的传奇历史,作者没有将马帮游击队塑造成完美的英雄,而是以“读者”身份切入到“历史”中,用文字探索人性的深度,追求灵魂的高度,探讨人类的终极意义。
自流井和贡井两个产盐区的合称就是今天的自贡,这里的交通、运输、商业、金融、文化、教育、卫生、以及城市的职业构成、社会意识、政治风云、生活方式等等,无不深刻地打上盐业经济的烙印,是盐塑造了自贡这座城市。如果说城市之魂在于文化,那么井盐文化就是自贡的灵魂,最能代表自贡的地域文化特色。地域文化是在一定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下形成的具有个性特质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它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的表现。
井盐文化作为自贡文化的代表,第一层底色便是被自贡本地的盐所铺染,特别是第一次“川盐济楚”以来的井盐生产史,它是井盐文化的主要来源。这一时期自贡盐业生产高度发展,在国内大多数地方还处于农耕社会阶段,自贡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工业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城镇,具备了工业社会的雏形,正是这种工业文明的影响使井盐文化具备了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同的特质,从而站在了更高的历史起点上。
如果说井盐文化的第一层色彩来自于地下的盐,第二层色彩则来自于移民文化的影响。从本质上讲,自贡是一个移民城市,自元末明初开始,特别是“湖广填四川”以来,几百年间,大量的外来移民先后进入自贡地区。在清乾隆后期,由于四川井盐业所推行的“听民穿井,永不加赋”的盐业政策,吸引了以从事盐业运销的陕商,开办金融业务的晋商等外省商人的大量涌入,在极大地促进井盐业发展的同时,也推进了各地域文化在井盐作用下的交流融合。
正是这些历史文化沉淀的相互融合和发展,在不断丰富井盐文化内涵的同时,也极大地延伸了其外延,形成了井盐文化独特的表现形式,在平凡与寻常中体验非凡的劳动和生活之美,在民族危亡时刻表现出来的奉献和担当精神。作品以自贡人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大时代背景入手,以新的视角去关注抗战时期那些盐商、盐工乃至盐马帮们的生存状况,感受他们生存中的酸甜苦辣以及他们生活的趣味,感受他们奋斗时的艰辛与不屈的精神,对井盐文华做出了新的诠释。
在小说中,随着滇西战役的惨烈对峙,盐商王四大人接到了昆明盐店胡总管给他发来的一封鸡毛信:“近因日寇疯狂侵占我东南沿海一带,海盐无法进滇黔,故已造成旷日持久的盐荒。军民无盐,苦不堪言,无力抗战,盐店的存盐早已告罄”。面对如此局面,盐商王四大人没有做出发国难财的的决定,而是找来马锅头云龙速速运送井盐去前线,在王四大人能装多少装多少的指示下,盐马帮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作者巧妙地通过临行前一晚马帮兄弟们在酒桌上的对话,向我们描述了自贡社会各阶层为抗战捐款的感人场面,妓女醉海棠还带头把自己卖身的钱都捐了,叫花子把讨来的碎票子也全捐了。自贡做为抗日战争中捐款额度全国最高的城市,记录在国民党军方公开后的资料中,至今保留在釜溪河北岸的“还我河山”就是当年国民党著名将领冯玉祥为富商捐款之善举所题写。在作品中彰显出的“位卑未敢忘国忧”的倾力奉献和牺牲精神,把自贡这座城市提升到了中华民族优秀样板的境界。
我们没有看到赵应陶醉在自贡丰富的地域文化特色中,而是更关注他笔下马帮的命运,探索袍哥人物的精神世界。在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对马帮文化和袍哥文化有深入地研究,特别是对袍哥组织的帮规、行话、习俗、轶事等做了详细阐述。袍哥会发源于晚晴,盛行于民国时期,与青帮、洪门为当时的三大民间帮会组织。作为当时四川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在其他地区被称为哥老会。在清代袍哥会在四川只是少数人的秘密组织,辛亥革命之后,它长期成为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直接加入或者间接受其控制的公开性组织。新中国成立后袍哥组织被彻底清除,作为一段史实湮灭无闻,不见经传。作者在深入研究史料的基础上,找来解放前自流井袍哥大爷王大爷喝茶吹牛,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由此,一个一个为了生存,不得不抱团加入袍哥会并被袍哥组织控制的马帮人,从历史深处走了出来。
从作品创作的艺术方式上,作者将政治的意识形态摒弃于外,不在政治价值的取向上做文章,侧重于从道德与伦理的角度对袍哥形象进行刻画,让袍哥在自身的行动中进行是非曲直的判断。如石门寨寨主袁三刀被云虎除掉后,云虎戏剧性的当上了寨主,都是占山为王的土匪,但两人给读者的印象完全不同。袁三刀匪性暴戾,经常下山抢劫四方,更是对过往的各路马帮从不放过。云虎作为袍哥,在遇见同门师兄云龙后,佩服师兄到抗战前线,得知自己的母亲被日本飞机炸死,国仇家恨更是激起了这位袍哥的血性,用炸药炸掉了多少年来殃及百姓和祸害无辜的石门寨,率领山寨弟兄随盐马帮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作品中赵应将袍哥大爷从过去“恶丑” 的形象中解脱出来,向俊美、仁义方向转化。作为一本新历史主义小说叙事的文本,因叙事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化,袍哥大爷的形象亦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既“恶”且“丑”的袍哥大爷形象被本性善良、有人性、重情义的新袍哥形象所取代。当云龙运盐走进云南滇西布依族村寨,让布依族少女阿花凝神的目光弄得脸红耳赤,显得窘迫的耷下眼帘。当阿花要将自己献给云龙时,云龙却在心里说:“云龙阿云龙,你狗日的千万莫糟蹋了那还没有开放的花哩!”后来阿花被日本鬼子杀害,妹妹阿朵再次要将自己献给云龙时,云龙轻声得对阿朵说:“你憨,憨哩!哥我哪能乱碰一朵花呀?!”今天的许多正人君子,在这里与之相比恐怕也相形见绌,我认为这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一种人性的追求。
《盐马帮》作为一部新历史小说的探索之作,在于它不是简单地用文学去反映历史,而是用一种完全崭新的历史意识去解读“历史”,是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的写作模式,标志着一种新的历史哲学意识的生成。美国詹姆斯•哈威•鲁滨逊认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兴亡,小到可以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虽说对以往发生的一切都可以纳入历史范畴,但是我们常说的“历史研究”只与重大历史事件、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其“历史记载”的大部分笔墨都用在了对内容的记录上,使之成为正史。与之相反的是民间的野史,它重点关注的是正史中不屑于关注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情感世界、生活情趣等。
赵应在作品中没有热衷于描写滇西战役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问题,更多的是凭借个人生活经验创造出来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是虚拟的故事,表现的是盐马帮人日常生活中的情景。虽然从题材上我们可以将作品贴上历史的标签,但实际上赵应在后记中已明确告诉我们《盐马帮》是虚构的,而支撑这些虚拟历史的是广为流传的民间观念,可以说,作者是在用文学的形式来展现历史,表达自己对历史与文化的思考,即历史为何会以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
正如苏童在《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活》、《武则天》等小说中想表现自己对历史的想象和虚构,用他自己的历史叙事模式去解构历史、重述历史。在他笔下,历史不再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来表现自己,而是将历史本身作为一种材料,是作者借以用来创作的叙事元素,这就是新历史小说的一大特点。在《盐马帮》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历史的解构、展现了现代人类的一种新的历史观念,这也应该是源自于赵应内心深处的一种观念:历史是无法被人把握的,但是可以成为你所想象的摸样,这无疑瓦解了人们对历史客观性和必然性的信心。可以这样说,《盐马帮》这部小说试图用一种解构的方法瓦解我们头脑中对历史的传统认识,去改变我们对传统历史小说中“大历史”和“大场面”的喜好,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去重塑“历史”,旨在告诉我们——“历史”是由平凡的老百姓演绎的,它应该表现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
阅读赵应的小说是愉快的,在这种愉快的体验中,让我感觉到作者在文学创作中的坚守和执着。作品背靠民间传统,将将民风民俗,江湖习俗演绎得非常精彩,人物形象塑造上各有特色。作者关于历史和历史叙事的思考,探索文学的书写从宏观叙事走向新历史主义的心灵史、微观史与个人史的微观叙事,可以说其作品也是面向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