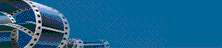一
《林红燕散文一组》在本刊去年第四期发表后,先先后后听到一些好评,而且似乎正在发酵,文学圈内外好些场合都有人提起。一本地市级内刊受到关注,这是近年来很少有过的事情。这与二十年前,谁谁有一篇过得去的小说、散文或诗歌发表,那种奔走相告的情景,多少有些相似。
林红燕的散文,首先是好的文笔,读上两句,就觉有味,不忍释卷。还有就是懂得节制,剪裁适度,不婆婆妈妈。思维活跃,不就事论事,在艺林中跳脱自如。常有出乎意料之笔,如行山阴上道,忽见柳暗花明,让人叫绝。读她的散文,那感觉犹如春阳透过冬日的阴霾,如晨风中挂在草尖上的露珠欲滴,如大梦中觅得久违的亲人,如与古今聊神作促膝谈。
林红燕虽是本刊的新作者,但绝不稚嫩。她看电影,听音乐,摄影,绘画,习字,旅游,读书,偶尔写一点东西,有一点“临水照花”的感觉。在一起喝茶,记不清她说过话没有,眼神内视。她是活在自己世界的人。自话自说,她的散文就是写给自己看的。她不是复制他人。印象中,她用自己略带神经质的目光睨视此在的世界。西湖早已被人写过,至于爱情、死亡,更是永恒的话题。她好就好在不是求同,而是求异,让自己的笔跟着感觉走,跟着思绪走,信马由缰,在文学的原野上不知所踪。
二
《林红燕散文一组》共六篇,前四篇是写荷花与西湖的,后两篇是写爱情和生命的。实际上是两组不同题材的散文。题材内容丰富些,在更多的领域试笔,对于作者和读者都有裨益。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先看看前四篇的落笔、布局、延异、与作结,看看林燕的散文有什么特色,或者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荷的残笺》并非写西湖。从一幅以“败荷”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写起,写张大千的墨菏,再联想到朗润园的“季荷”,记起季羡林所说:“荷在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领悟生命的轮回。
《西湖雨》写西湖雨中摄影,一步一景,美不胜收,感叹《西湖美景》商家的造作;以过半的篇幅写在虎跑泉品龙井茶,体味周作人名言:“一壶清茶,约三五知己,得半日清闲,抵十年尘梦”。
《西湖水,花巷鱼》,与其说是写西湖水,倒不如说是写西湖的“人”;断桥的邂逅、苏小小的才情、一对新人以西湖水为背景的婚纱摄影;写花巷鱼,写“半江瑟瑟半江红”的奇景,再由西湖醋鱼,联想到苏东坡的美食创意。
《西湖花,灵隐石》写西湖花,由曲院风荷,写到花巷牡丹,由一株古梅,联想到梅痴林逋;写灵隐寺飞来石,写摩崖石窟,触摸远逝的历史,悟出:“女人应该如花开时的瞬间灿烂,更应该如石头般恒久厚重”的道理。
细读这些篇什,行云流水,藏露掩映,随意点染,迁想得妙,我们感受到的是作者的文笔与学养。这是一个有相当文学积累的人:与大师的神交与碰撞,没有掉书袋的痕迹,古典诗词的化用,信手拈来,语义翻新。这是一个有绘画摄影天赋的人:所绘之景无不诗情画意,对声光色影的捕捉,联想、通感、腾挪、留白的移用,妙趣横生。这是一个讲究生活情趣的人:品茶、饮食、旅游、摄影、阅读、交友,谈玄、看电影,生活于既传统又现代之间。这是一个既浪漫又敏感,常常把自己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祭爱》、《祀鬼》两篇,在貌似平静的叙述中,对爱情和生命的痛彻心扉思考,犹如一把看不见的解剖刀游刃于灵与肉的断裂声中。
雍容,婉约,缜密,深刻,近年来,这样的散文小品已不多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史散文、学者散文勃兴,散文随笔越写越长,动辄上万字,几万字。而这类随笔,基本上是内容压倒了形式,成为历史的考据,人物的别传,或者时政的针砭,哲理的演绎,不一而足。我个人倒是喜欢这类“大散文”,但散文小品的贫弱,毕竟是个遗憾!
三
由是想到了鲁迅杂文《小品文的危机》(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六期)。文中写道:
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
鲁迅这段话的意思,一是五四运动散文小品的成就,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二是肯定五四散文小品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三是指出白话散文在五四落潮以后已经跌落成为“小摆设”了。
于是,新旧营垒众口一词地发出“小品文的危机”的警示。糟就糟在这“小摆设”!鲁迅极端刻薄地羞辱道:
想在战地或灾区里的人们来鉴赏罢——谁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梦。这种小品,上海虽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这里被骂的,当有他的胞弟周作人、特别是曾经的同事林语堂(鲁迅把小品文称为“小摆设”的批评,所针对的其实恰是林语堂创办的《论语》)等人。鲁迅在文终开出了解除“小品文危机”的单方: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四
透过鲁迅匕首投枪式的语言,依稀可见先生横眉怒目的样子。林语堂等人欣赏的是晚明小品和六朝散文的“闲适”,那是文学上的一种“小摆设”,而鲁迅却看到唐末和明末小品的抗争和愤激,“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当时正是山河破碎,民生凋敝,“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艰难时世。从1934年起,鲁迅明确用“杂文”指称自己的文章,小品文与杂文,闲适与抗争,从此分道扬镳。如今时过境迁,重温八十年前关于散文小品的这一段公案,不免感叹于鲁迅先生态度的决绝,又略感对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多少有些误读。
类似的争论似乎始终没有中断过。延续至今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关于大散文“大散文”与“艺术散文”的论争,即关于散文文体的论争。
1992年,贾平凹在《美文发刊词》中写道:“我们的杂志挤进来,企图在于一种鼓与呼的声音: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散文!”这是“大散文”的第一次书面宣言,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却发在《美文》这样的刊物上,须知“美文”比“小品文”更考究,更注重形式啊!
姑且不管贾氏的宣言与“美文”自相矛盾,但以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历史随笔、哲学随笔以至时政深度报道为主的“大散文”,确确实实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已经式微的散文原野。这类大散文,强调散文的大境界、大气象、大手笔:内容上要求呈现出大气魄、大制作、大景观,展示才识、胸襟、气度与使命感;艺术上要求突破题材、结构 、手法、语言等方面的限制,尽可能扩展散文的艺术表现手段;形式上主张允许“跨文体写作”,甚至辅之以照片图片等等。
而那些职业散文作家,则主张“净化散文文体”,倡导“艺术散文”,煞有介事地要对时下的散文“清理门户”。什么是所谓艺术散文呢?余光中说,“我要讨论的,是另一种散文——超越实用而进入美感的可以供独立欣赏的创造性的散文。” 郭枫在《探索散文的艺术奥境》一文中以立法者姿态作出了界定:“应专指具有高度创造性之艺术作品,即以文学手法写作,创造高度艺术美,故为纯文学作品。普通随笔、杂谈之类,多以实用为目的,以描写事物表达己见为满足,不具艺术性质,应称之为‘一般文章’或‘实用散文’,自然不属于纯文学性质。”
随着九十年代“散文热”的降温,以及对真正大散文的滥觞者余秋雨的讨伐,散文界出现了一个非常具有反讽意味的奇怪现象,那些对余秋雨恨得痛心疾首,必欲诛之而后快的“十字军”作者,都写起动辄数万、甚而数十万、成系列成建制的散文随笔,这是一个非常闹热的文坛景观。精明的出版商早就嗅出,这类“大散文、大随笔”,其销路要强于纯文学的诗歌、小说。“双赢”的奥秘就在这里。
五
文无定法。苏东坡在《答谢民师书》写道:
(行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词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苏东坡对散文的要求是“文理自然”,“如行云流水”。要达到这一高度,第一个层次是“求物之妙”,“了然于心”,这是讲观察、积累、消化、神会的过程;第二个层次是“词达”“文胜”,“姿态横生”。 作者情思美妙,表现得心应手,则文章自然会有简洁、自然、轻灵、飘逸的风格。而要达到如此境界谈何容易?
苏东坡在《跋退之送李愿序》中写道:
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余亦以为唐无文章,唯韩退之《送李愿归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
这又是文坛两段千古公案。公允的看法是,《归去来兮辞》、《送李愿归谷序》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同时也因论者的角度、语境,放大了自己的偏好,显得片面和武断了些。但“为文要有千年之想”,这两则“极评”的积极意义也在这里。
我之所以把先贤、经典抬出来,无非是想论证,我们这个散文的泱泱大国,有丰厚的散文传统,即使是被贬为“小摆设”的小品文,也有它存在的理由。“小摆设”没有什么不好,它们美化生活,投射主人的品味,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的审美情趣,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至今读来仍让人心往神驰。以我之见,五四以来的散文小品是最见作者功力、情致、气度、学识的一种文体,绝非西方随笔、杂谈、传记、时论的新闻文体所能代替。在流行大散文的当下,我十分乐意呼吁“回到小品文”。并以此给林红燕这样的文学新人鼓鼓劲,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散文小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