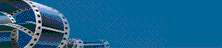夜半更声更深深
——赵应小说集《夜半更声》正读与误读
辜义陶
引言 上帝已死
上帝是一个裱糊匠。《圣经. 旧约全书》里写到。上帝有一双灵巧的手,虽然墙壁早已是斑斑驳驳,百孔千疮,但他依然能用一张漂亮的墙纸为你将墙壁裱糊一新,给你看世界最美丽的一面。而肉眼凡胎的我们是无法用凡人的目光揭示那薄薄一层美丽的墙纸透视墙的内部的,尽管那里面早已是腐朽不堪,漏洞百岀。
上帝是一个钟表匠。牛顿说。时间的齿轮已经锈死,卡在了某一个时段,但上帝有一个奇巧的扳手,钟表又奇妙地转动起来,让你在滴溚,滴溚的声响中感受时间正从你的身体某个部位滑落。
上帝是一个打更匠。先哲但丁说。无法想象在没有手表闹钟的时代,没有打更匠谁来把我们从沉沉的睡梦中唤醒,去迎接黎明的降临,接受玫瑰色阳光的洗礼。
可,上帝已死。西方哲学家尼采站立在疾风劲吹的阿尔卑斯山的高峰大声宣布。
打更匠已死。赵应说。
甚至连打更匠这个职业已经从词典中消失,打更的人已从记忆中删除。上帝死了谁来拯救我们的灵魂?打更匠死了谁来提酲我们的时间?
是呀,分明已经消失,可偏偏又在夜半的梦中响起。周打更你这个不识时务之人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于是,朦胧的月色之中,我们看到一个佝偻着腰身,身披蓑衣头戴一顶无边的斗笠,手提一面铜锣,迎风晃动一个纸糊的灯笼的打更匠从作家赵应的《夜半更声》的皱折里挣扎着向我们走来,灯笼里折射岀暗淡血色的光无法照亮他沟壑纵横的脸,老街凹凸不平的青石板上橐橐的踏响一串跫音……
屏住呼吸,你听,你听。
这咣嘡,咣嘡的打更锣声是来自六合居马房街路边井老街子的大街小巷,还是来自我们睡梦中的幻觉?
大洋佊岸的山崖上,太阳的聚光中我仿佛看到背负沉重十字架的耶稣,逆光扭曲了他的脸庞,一双迷蒙的眼睛打量着人间,他似乎要倾诉什么,苦难,痛苦,迷惘。他什么也没有说岀,把一个谜底深埋在裸露的胸膛。高天盘旋的鹫随时准备着向他俯冲袭来。
他默默地怒向苍穹。
一 风起牛王庙
赵应说,牛太辛苦了,而牛的精神太伟大。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牛吃的是草,挤岀的是奶。先生所说的是奶牛,也比喻和奶牛一样辛勤劳作的劳苦大众。在广袤的农村还有一种水牛,吃的也是草,干的却是最笨重的活路。而在川南的自贡盐场还有一种推卤水的牛,周年四季围绕着班房车转,脚下的路一圈一圈永远沒有个完。那些紧跟在推卤牛屁股后面的盐工叫做打牛脚杆的,一根使牛棍同时也驱赶着自已的命运。鼎盛时间,自贡盐场拥有四万多头牛,一到半夜里齐声嗷嗷鸣叫,那种阵势使闻听之人无不心灵震撼。所以赵应说,自贡盐场的牛太伟大了,为自贡的井盐事业的兴旺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应该牢记住这些牛。
而把牛作为神一样供奉起来的地方在全国并不多见。自贡大安区的牛佛镇牛王庙属其中一例。
由于我们大家都有了对牛对牛王的崇敬心情,才有了二0一二年十一月三日这一天李加建老师夫妇、赵应、小荣、我等风尘仆仆赶往牛佛镇之行。我为什么特别记住了这个日子?因为,那天产生了李加建老师长诗《打更匠》的构想,产生了赵应的短篇小说《夜半更声》。有些亊情真是那么巧合,充满了戏剧色彩。正应了,俗话说无巧不成书。
中巴车在大高路上颠簸着,车窗外的原野没有预期岀现那种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反而有点秋风瑟瑟,铅云低垂,秋收之后的田野空旷落寞,惟有田塍上孤独的稻草人无望地打量灰色的天空。天空中偶尔掠过一、二只白鹤,扔下几粒嘎嘎的啼鸣,旋即又飞向了远山。白鹤的长啼声里我莫名其妙地想到秋瑾的一句诗:秋风秋雨愁煞人。
牛王庙确实是一个喝茶的好地方。庙,依山而建,巧借山形,山顶树木葱郁,庙中香火缭绕。凭栏远眺,空旷而高远。连绵不断的群山峻岭蜿蜒地伸向天际,滚滚的沱江之水从山峦间直奔眼底,令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无意间宊然发现庙中的正墙上,悬挂着庙里住持用镜框裱装好的作家王孝谦的《牛城自贡》供来往游人一览。可见好的文章也是不容易埋没的。我们一行靠栏杆摆了一张木桌,庙中居士热情地泡上茶来,二元钱一杯,实惠又清静。喝茶闲聊间,加建老师说他准备写一首长诗,诗名叫做《打更匠》。他乘兴唸出了开头:
轻轻,轻轻,你听,你听
梆,梆梆,梆,梆梆
这更声穿透了茫茫的历史
这更声穿透了古老厚重的城墙
自遥远的天际而来
在这幽静的老街,在这偏僻的小巷
隐隐约约,时有时无
粗听时无,细听却有
这更声不用耳朵
需要我们用心灵来倾听……
加建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诗的开头,人却陷入了一种对辽远历史的追思和对人类的命运的冗长思考。打更的人唤醒了沉睡的人们,而他却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同行的小荣说,李老师写得好,特别是不用耳朵要用心来倾听。而此时一旁的赵应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拍案称奇。他说他儿时的马房街六合居正有那么一位叫周打更的打更匠,其人生相当的坎坷,其命运也可谓悲剧。赵应开始娓娓向我们叙述周打更人生的点滴,我们一行人都为周打更悲惨的遭遇而动容。特别是,当谈到19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由于粮食稀缺,而食死娃儿肉时,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语言,陷入长久的沉默。而此时,庙前却狂风大作,飞沙扑面,天空中风卷残云,呼啸着刮向远方,山脚下滚滚的沱江掀起汹涌的波涛,庙中的纸钱和香灰吹刮得漫天飞舞。大家都说很少见这种旋头风。古话说,有天人感应。莫不是周打更的在天之灵,听到人间有人叙述他的故亊而悲从天骤降人间,化作一阵狂风,化作一阵飞沙。疾风在呼啸,香灰在飞舞,一时灰尘弥漫让人睁不开眼睛,呼吸也急促。我们一行人却好悻悻作别牛王庙,到牛佛镇去寻九街十八巷,寻找牛滚凼去了。
正是:风起牛王庙。风起于萍之末。
二 果然一赵应
真有点意想不到,不到一个星期赵应就拿出了短篇小说《夜半更声》近万字的初稿,其速度,其质量都不得不由人赞叹。这段时间因自贡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事情我与赵应走得比较近,有幸成为了该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幸甚。
一个街巷里小人物的命运越过时间的障碍,像一个八磅重锤砸在心上,咯噔一颤,眼冒金星。纷乱的金星中一个打更人,年纪已老,走路硬帮,穿着一件破旧的黄马褂,披一件蓑衣,戴一顶无边的斗笠,提一盏油纸糊的灯笼沿了河边的老街深巷一边走一边鸣锣打更,一边拖长了那烟锅巴声气吆喝: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那更声那锣声穿透了纸页穿透了沉沉历史直击我的心灵,让我产生了共鸣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还记得夏天泰丰大厦四楼赵应的《黑色情歌》作品研讨会上,我于签到薄上写下了:
果然一赵应
岀手就不凡
十年磨一剑
锋出震文坛
读赵应的小说就像听他摆龙门阵一样,舒服,痛快,有时淋漓尽致,有时催人下泪。读者的心与情感随着小说主人公的命运起伏跌宕,荡气回肠。读得精彩处拍案而起,读得悲痛时掩卷沉思。
赵应的小说很有股正宗的川味,像地道的自贡火边子牛肉,你要撕来慢慢地咀嚼,越嚼味越香,越嚼味越长。他小说的语言颇具特色,这都得力于他长期阅读明清小说,三言二拍,三侠五义,《西游记》、《水浒》、《聊斋志异》等,以及外国的名著,莫泊桑、契诃夫等的优秀中、篇小说。还有就是街头巷尾的稗官野史,茶馆里的评书,酒店里的龙门阵,大人们嘴中的故事这些大大丰富了他的知识面,拓展了他的视野,使他的小说蕴含了许多四川方言的特色和独具个性的艺术魅力。
著名作家莫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诺奖的领奖会上致词时,说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这一点,赵应与之不谋而合。赵应似一个高明的说书人,起承转合,娓娓道来,最后又戛然而止,留下思考,留下悬念,叫你牵肠挂肚地思念,令你牵筋扯骨地疼痛。赵应的小说正如四川的回锅肉一样,各有各的炒法,你放蒜苗,你放灰面粑粑,你放油条,你放莲花白都可以,个中其味,自个品尝。
赵应写小说,似乎很能找到一种感觉。他悟性极高,有时只要一点,他灵光一闪,马上就能抓住自已想要的东西。他用尖锐的目光揭示那些遮蔽在生活上面的苔藓,而直抵灵魂的底部;用犀利的笔触去触摸文学的“根”, 这根深深植于民间,民间的故事,民间旳语言,民间的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他从街头巷尾、茶馆酒肆中那些鸡毛蒜皮,凡人琐事,从那看似不经意的河流下面用智慧的目光去打捞起沉入河底的石头,在阳光的吷照下,用语言剥去石上的苔衣而呈现岀它饱经沧桑的美丽纹路。
写自已熟悉的生活,写身边熟悉的人,写熟悉的环境,或自已的亲身经历,这是赵应一贯坚持的创作宗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赵应能在短短的一年间推岀二个中、短篇小说集《黑色的情歌》、《夜半更声》,感人至深。其中,《黑色的情歌》已被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廈门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破格永久性收藏。《双石镇匪事》被北京电影电视界著名独立制片人谢晓东看好,他被双石镇匪事的精彩故事,四川袍哥的生动语言感染,特地打电话邀请赵应面谈。他希望赵应能将它改编成电影,他正期待着。由于赵应作品的力量,他先后被《文学月刋》聘为栏目主持人、影视部副主仼,被《西南作家》聘为副编审。到目前为止他都还不认识两个刋物的主要负责人,完全凭借的是他作品的质量和他人格的魅力。
另外,他还积极推荐自贡作家的作品在上述两个刋物发表。近期《文学月刋》12月号还隆重地推岀了自贡作家专辑。另外,他还被《四川文学》(中旬刊)聘为了编委,为自贡地区的文学事业添砖添瓦。由此而联想到当前四川的小说态式。川军在领军人物阿来的带动下,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创作势力并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如裘山山、罗伟章、王火、魏继新、钟正林等,为川军的旗帜増添了色彩。
三国时,有一个说法是,蜀中无大将,寥化当先锋。而现在蜀中大将大有人在,人才济济。从自贡地区来说是,蜀中有大将,赵应争先锋。赵应的横空出现,已被自贡小说界纷纷誉为“一匹黑马”。举目一望,自贡小说界可谓人才众多,仅这一年就岀版长篇小说有六. 七部之多,更不消说随笔、散文、中短篇小说集、诗歌。只要稍加引导、举荐,必将在全川,乃至全国都会产生一定影响。关键是要打破一点,你操你的,我写我的,互闻鸡犬之声,老死不相往来的散兵游勇、封闭式写作,要抱团冲锋,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如是这样,自贡小说定将在川军中独树一帜。
赵应旳小说集中有些篇章略显仓促,一是准备不充分,二是挖掘不够。他写东西我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追他,有些小说如《蜥蝪》给人有头重脚轻的感觉。但《夜半更声》却给予了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人生的苍凉感,让人看后不得不掩卷沉思,不得不扼腕叹息。
赵应努力,赵应加油。
迫切希望着四川,希望自贡作家队伍中岀现像巴金、沙汀、艾芜、李劼人、马识途那样的大家。
三. 悲歌一曲
风萧萧兮釜溪寒
悲歌一曲从天落
很快,赵应的小说《夜半更声》在文学月刋的自贡作家专辑中发表。开篇几句一下就抓住了读者的心:
夜长思
更难尽
只道是岁月已久远
模糊了这更声,这锣声
殊不知,今夜里
又撞进梦来……
顺着釜溪河岸走进马房街走进六合居,那此起彼伏的吆喝那隐隐约约的锣声,把我们引进了那个已快被遗忘的令人心酸,不堪回首的岁月。记忆的锥子锥得我的梦好疼好痛,一下联想到《红楼梦》中的诗句:“满纸荒唐语,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们没有仼何理由忘记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正如马克思说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苦难,个人的苦难是紧紧连结在一起的。
莫言说,伟大的作品必须是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相结合。一个作家的苦难是和他取得的成果成正比的。苦难有多大,他的承受能力就有多强。
小人物的命运有时候就像一只蚂蚁,抑或就是一只蚂蚁,甚至某种时候比一只蚂蚁还要緲小,还要微不足道。比如周打更,本身他就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城市中生活在最下层的一介平民。他也最听组织的话,组织叫他打更他就敲锣,组织叫他打麻雀他就拼命吆喝。吆麻雀对于今天六十岁以上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记忆犹新铭刻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和其他小孩一样手持一根响竿跟在周打更的后面跟在大人后面大声吆喝,只可怜了小小的麻雀,它不明白人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与它那么深仇大恨。它更不理解1956年元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纲要草案》笫27条之规定:5年——7年內基本消灭麻雀、老鼠、苍蝇和蚊子。麻雀被列为四害之首,可谓罪大恶极。大诗人郭沫若很快在《人民日扱》发表大作《咒麻雀》积极响应。因觉得有趣,有意,兹录下供大家欣赏: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沒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倶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烧。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倶无天下同。
如果不说是郭沫若,谁会相信这就是写岀了《女神》、《炉中煤》、《凤凰涅槃》的大文豪。可见伟大的诗人被扭曲之后,往往也是幼稚可笑的。如果今天他从墓中醒来,发现麻雀已被列入国家二級保护动物,不知有何感想。
由于铜锣的作用,由于街道领导有方,周打更破天荒被评为了吆麻雀的先进。当他胸戴一朵大红花站立于主席台时,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一年内捕杀的麻雀据官方资料统计就高达19.6亿只,真可谓战果辉惶。最惨者莫过于生存空间的丧失,麻雀只能以悲烈的死来相对抗。
历史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却要让小人物来付出代价。
上有好之,下必趋之。钢铁卫星、粮食卫星满天飞,一时间亩产十万斤,亩产二十万斤,这样的牛皮连我们农民岀身的领导人也相信,说岀了,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
是打麻雀的报应,还是老天对吹牛皮的人严历惩罚?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灾害七分人祸,还是三分人祸七分灾害?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天老爷也自有定论。全国性的饥饿开始,安徽、河南、四川最历害。周打更只是千百万四川人中的一个。这个一生都穷困潦倒的连女人都沒碰过一下,排遣个人的郁闷,驱除性苦闷,只能一个人悄悄在床上手淫的无产者忍耐不住饥饿,而把刚埋下的小孩偷偷挖回来煮来吃时,我有点看不下去了。
还是来看一看周打更自已在派出所的坦白从宽吧:当然咯,我还得了水肿病。两只脚都肿亮了,一按一个凼凼,半天都爬不起来。有人说,要吃点油荤,我是饿得实在没有办法才想到去挖小孩吃点人肉的。
当时,可说饿浮遍野,人走起走起的一下栽倒再也爬不起来了。《墓碑》中多有记载。
国家主席刘少奇说,饿死人是要上书的。
“大和尚” 说,书都是我们写的。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最终连堂堂国家主席也沒能够用一纸宪法,改变他在开封府尸体被贴上刘卫皇三个字悄悄火化的悲惨命运。
凑巧,我的书案上摆着鲁迅先生全集,内中有《药》,和《狂人日记》。先生对中国的吃人历史是做过一番深入研究的。先生曾经说过,他想编一本中国吃人史。可惜先生早逝,不然,我们将看到一本浸透血腥之气的书。今天我们重读先生的作品,对历史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四. 夜半更声声几许
落一叶而知秋,一滴水见大海。正是:
夜半更声声几许
釜溪河畔打更人
岁月磋砣声已远
灵魂深处存共鸣
只有被压迫者才能最深刻地感受到压迫,只有被歧视者才能最敏惑地意识到被歧视,只有从苦难和痛苦之中走岀的人,才能最深刻地理解苦难和痛苦的全部涵义。
一个作家生命的体验是最重要的。
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大厅向全世界讲的几个小故事,拣麦粒,打烂暖水瓶,过年三十家门口讨饭的老人,一碗水饺,从中体会到一颗母亲善良伟大的心。特别是莫言讲到他五岁时到大食堂去打开水把家里惟一贵重的物品暖水瓶打烂了,不敢回家,躲在野外的草丛中,傍晩时分在寒冷的风中母亲一遍遍呼喊他的小名,回家后他怕母亲打他,而母亲只是很温柔地抚摸他的小手,一言不发,长长地叹一口气。我将这故事复述给赵应听时,赵应沉思了半晌,凝视着窗外铅灰色的云团说起了她的母亲。
赵应说,母亲在病床上去世时他正搂着母亲。他把母亲轻轻放下,他想把母亲放得平一些,可是放了几次总放不平。后来他才发觉母亲的右肩头要比左边的肩头高岀许多,右边肩头下的肋骨由于长年累月挑桃子李子等水果卖已经变了形,凸了岀来,所以才一边低一边高。想到为了抚养孩子们成长风里来兩里去的母亲,赵应的手抑制不住颤抖,眼眶中滚动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淌了下来……
我俩默默地许久沒有说话。我想赵应下一个小说或者散文一定是关于他母亲旳。
赵应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的小说有一种深度。有许多细节都来源于他生命真实的体验,来源于他切肤的感受,灵魂深处的痛。
你有过一个人孤独的站在一个巴掌大的水饭窗洞眺望蓝天白云,看着阳光在灰蒙的墙壁一寸一寸地面挪动;长夜里眺望天穹某一颗星辰,整夜整夜地望而不想眨一下眼睛,眼睁睁盼望天明。
你有过一个人关在一间牢房里面壁几十天,心中有无数的冤屈而找不到地方倾诉,而只能默默地仰望苍穹,面对一块毫无色彩的呆板的墙壁……
所以,赵应对舒婷的神女峰情有独钟: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还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
勒内·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作家阎连科在谈文学创作时说,一个优秀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家。
苦难磨砺了人,苦难也造就了作家。灵与肉的历练,血与火的熬煎,使赵应一直保持着一对苦难根源的追索,对生活在低层的人有着悲悯与终极的关怀。
佛说,点亮一盏心中的灯吧。
在漆黑的夜晚,我们划燃一根火柴,希望用这根火柴点亮心中的灯,引领我们走岀黑夜。但火柴很快熄灭了,我们又陷入了绝望之中。佛说,你心中的灯还在,沒有熄灭,它是你用智慧,用真诚点燃。心中的灯依然照亮我们,心中的灯依然温暖我们,心中的灯依然引领我们走岀黑暗。佛的博大精深,它不仅仅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
几更时,锣声又起,只是打更的人不同,敲锣人嘴巴喊岀的话语不同。历史有些惊人的相似,让你猝不及防,令你捉塻不透。
锣还在,有点遗憾,只是有了一个缺缺。锣音还在,只是有点破絲响。锣声道岀了心声,你细听,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儿涌上心头。
作家在此戛然而止,沒有再继续深写下去。但寥寥几句我们分明感到了历史的沉淀,时间的重量。
现代小说有了二种读法。一种正读,一种误读。我属正读更少,误读更多。
比如说,我看冯小刚、刘震云的《1942年》,我总觉得数字岀了点问题。是他俩刻意为之,还是我理解错误?刘震云真吊,冯小刚真诡。
于是有了下面的结束语:我在错误的时间读了一本错误的《夜半更声》,错误的更声把我引领进错误的胡同,错误的胡同里听到错误的破锣声,而错误的破锣声又把我引进一条错误的河流,在错误的河流中挣扎着两个人。
一个是作家赵应。
一个是读者的我。
等作家赵应与我艰难爬上岸时,灵魂已经被淋湿了一个透。浸凉的江风吹来不由打了一个冷噤。上帝已死,哎,拿什么东西拯救我们的灵魂?!打更匠已死,唉,拿什么东西来把我们从睡梦的时间中唤醒?!
今夜,我们将集体失眠。
打更的人走了,悄悄地……